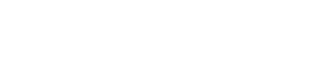太瘋狂了(原創機甲賽羅怎么畫)原創機甲獵人,
原標題:“機械”之變
王如晨/文

“蘇東坡一日退朝,食罷,捫腹徐行,顧謂侍兒曰:汝輩且道是中何物?一婢遽曰:都是文章。坡不以為然。又一婢曰:滿腹都是機械 。坡亦未以為當。至朝云,乃曰: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 。坡捧腹大笑。”
明人曹臣《舌華錄》“慧語第一”中的一則語錄。
朝云情商夠高,表達也生動。難怪甚得蘇東坡喜愛。

但這里更想說“機械”一詞。
文中奴婢二所謂“滿腹都是機械”之“機械”,出于奉迎,稱贊蘇大學士多才多智。不過,這詞日常用于人、事時,多形容機巧奸詐。色彩強烈時,基本就是“一肚子壞水”。
這種詞匯的色彩之變,由來已久。
《莊子·外篇·天地十二》。子貢游楚返晉,過漢陰。見一老頭打理菜園,“鑿隧而入井,抱甕而出灌,搰搰然用力甚多,而見功寡”。
啥都從頭來。徹底閉環,封閉一體。既沒效率,也不經濟。
子貢說,明明有槔(井口吊水的杠桿),一日浸百畦,為啥不用。

老頭先強調了槔的構造與便利性。然后忿然作色而笑曰:“吾聞之吾師,有機械者,必有機事;有機事者,必有機心。機心存于胸中,則純白不備;純白不備,則神生不定;神生不定者,道之所不載也。吾非不知,羞而不為也。”
這邏輯在老子學說里,比比皆是。不過也不止老子。
君子不器于物。傳統中國人對器物、有形的工具愛恨交織。既能整出極為精密的工具與裝置、精致到腐朽的文娛化玩意,對于供給側有形而高效的器、工具的生成與改造,又天生充滿警惕。
這思維連綿不絕。想想到晚清,慈禧太后對火車的前后態度。。。。
不止有形的部分。無形的更多。凡是面對效率符號,都是如此。后者幾乎都會經歷污名化。
比如傳統中國對“商人”的認知。面對一種保守的文化容器、農耕經濟,后者可是一種顛覆性的力量。幾乎每一代易姓革命,背后除了基于土地的革命,技術/工具等生產力符號,都有商人、商業力量的助推。
實際上,上面的子貢,在孔子弟子群里,說是“言語科”一號位,擅長社交,實際上更是“商人”與“商業”的符號。甚至可以說,他是孔子的金主。子貢的段子很多了。

還有意識形態的東西。凡是有利于普惠大眾、直接撬動權力結構、穿透迷障的東西,上面就不自在。幾乎都會拖延落地,甚至直接禁止。
比如上古“絕地天通”。神話結構要代代維護,生怕下沉,普通人借此探得權力合法性的秘密。
“機械”一詞,就有多重含義了。它從有形的效率工具、裝置,開始被污名化,逐漸變成遠離甚至違背自然、真實、樸素、人性的符號,帶有較重的倫理色彩,甚至意識形態味道。
當然,“機械”一詞,是一種偏正結構,摳一下,確實也能體會到這種變遷。機械、機器、機車、機關、機事、機心,都是。仿佛藏著不可告人的人事的秘密。

后世一堆表達。
《漢書》描述始皇陵墓之下:“下錮三泉,上崇山墳,其高五十馀丈,周回五里有馀;石槨為游館,人膏為燈燭,水銀為江海,黃金為鳧雁。珍寶之臧,機械之變,棺槨之麗,宮館之盛,不可勝原。”
至今,民間仍流傳著這陵墓之下的種種機巧。
“機械之變”,一度成為一種相對固定的表達。我上面的標題,也是套用了班固一下。
它也近乎圈套、“局”或“甕”。
明人王樵《尚書日記》寫武庚的局。
“武庚雖包藏此心,而王室未有釁,則亦安從而發哉?不幸而三監者入其機械之中,為所扇惑。詩之所謂既取我子者,指此也。”
宋代及以前,“機械”一詞的色彩重得多。我其實比較比較喜歡它與自然的分立。
《宋史·列傳》說到“劉一止”:“一止沖淡寡欲,嘗誨其子曰:吾平生通塞,聽于自然,唯機械不生,故方寸自有樂地。”
這里的“機械”與“自然”對立,雖仍有形,但頗近本雅明“機械復制時代”之“機械”了。后者有效率,但已失去本真與自然的光暈。
今天,“效率”一詞,在商業社會,被拔高到無以復加。不過,人文的世界,很多時候,“效率”強調過度,是有反人性的指向的。一些美的東西,恰恰是通過審美制衡的中介才能實現。中介不等于中心或中心化。
當然,到明清,“機械”一詞,又開始向它的本義回歸。工具、器物、裝置、設備,背后對應著一個分工日益細密的商品經濟社會、前工業社會的演進。盡管思想理念中有種種保守,但我們在科技、軍事、農事、天文歷法著作中,仍能感受到工具理性的涌動。
關于中國科技為何后來落后西方,很多人用種種法論證過。在我看來,“機械”一詞的色彩演進里,藏著基本邏輯。
今天的社會,強調各種效率符號,強調AI、應用、技術普惠,尤其有形的機械、機器、設備、高端制造。芯片啥的標榜甚多。
還有,人才結構的指引。開始重新審視與機器、技能相關的基礎人才價值。若你看美國IT業,尤其一些巨頭的誕生,通常是一種整體氛圍中的DIY邏輯,它有基礎土壤與自由組合的生成。
當然,我們的指引背后,有許多壓力面在。包括所謂鉗制。不過,即便沒有這層,也到了一個周期。過去幾十年,你的DIY能力是為別人服務,是在別人的游戲規則里探索,它并不自由。今天壓力很大,卻是真正獨立的創新之路。
說遠了。回來。
我們當然樂見“機械”一詞向著本義繼續回歸。但最后還是得說,伴隨著有形的世界演進,我更希望我們無形部分尤其精神文化、心理世界的回歸。
其實,很多時候,“躍遷”、“升維”,不是升到高處下不來,吊在半空,而是兼容多個維度,除了向上、向前,還有向后。真正的回歸,也是“躍遷”。
“機械”一詞,無論色彩多濃,它從來不會失去它的故鄉。它只是在曲折反諷中通達自我,通達自由。
上面,與子貢對話的老農何嘗不是反諷呢。
現實中,若是一個為了生存的老農,怎么可能放棄他深諳機理的高效率的槔呢,那是他的家伙什。
而作為那個時代以及自身師門的效率符號之一,子貢面對他,又何嘗會羞赧而去。
他們不過是莊子為批判孔子理念而設置的符號罷了。“圃畦丈人”并非真正底層的“農人”角色,而是近乎隱士的角色。他的實踐看似清苦,實在不過是一種理念的身體力行。
老莊美學的精髓之一,就是通過重塑中介,扭轉他們那個時代過度的“效率論”。
畢竟,人世乃至整個世界并非為效率而生,這確屬是常識。
這種邏輯綿延至今,仍有它強大的生命力,并反復重現于現實生活中。很多時候,甚至會引發社會面的震撼。最近幾年的反壟斷,里面就有部分反互聯網效率的邏輯在。今日AI被強調過度,未來一定還會持續引發許多社會話題。而當下大熱的ESG思潮與實踐中,同樣隱含著回歸與反思的力量。

當然有種種爭議。而且,你也能看到,最近“效率論”重新回歸,聲量走高。它既是一個國家、社會、產業演進的結果,也是某種傷痕的修復。
兩種相反的動向在同一個窗口期閃爍。整個社會面糾結而顫抖,同時又有豐裕與樂觀在。
這才是真正的微妙之處吧。或者說,這是真實面吧。
突然想到錢鐘書《管錐編》第一冊開頭“論易之三變”旁征博引闡釋的“并行分訓之同時合訓”。為簡化標點計,這里不用直接引語,只重復使用他的材料。
《論易之三名》:“《易緯乾鑿度》云:‘易一名而含三義,所謂易也,變易也,不易也。’鄭玄依此義作《易贊》及《易論》云:‘易一名而含三義,易簡一也,變易二也,不易三也’。”
“易”之三義三位一體。“機械”之變,雖云及兩端,但從“機械”本義到機巧奸詐再到它的反復與回歸,何嘗不是"易之三變"呢。
我們也可以用辯證法的“正反合”來還原“機械”之變的邏輯。每一種社會思潮,每一輪產業的演進路徑中,都隱含著相反的力量。一俟過度,另一端就一定有力量傳遞過來,冷冷又熱熱,形成新一輪制衡。
在我看來,最有價值的部分恰恰在于,兩種動向在一個窗口期閃爍、交織。它才是真正的自覺吧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責任編輯:
注明:本文章來源于互聯網,如侵權請聯系客服刪除!